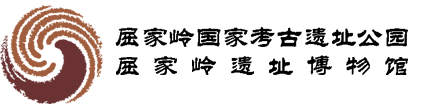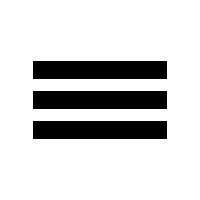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原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发掘6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的东河与西河之间,东河原名“石家河”。石家河镇,即得名于东河之原名“石家河”。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于1954年在配合石龙过江长水渠工程考古调查中,和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同时发现。
1954年底,笔者和同事程欣人一起,为配合湖北省石龙过江水库的水渠工程考古调查,在跨钟祥、京山、天门的长水渠工程线路上,共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100余处,多为新石器时代或是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遗址,其中有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较为密集。在京山县国营五三农场东南面的青木河与青木垱河之间,考古调查发现分布较为集中的屈家岭、毛家岭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天门石家河镇北的东河与西河之间,集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分布面积最大。
京山屈家岭分布较为集中的一片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京山的南部边缘地带,天门石家河分布密集的一片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天门的北部边缘地带,二者直线距离仅20千米许。
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只知道黄河流域考古文化中的仰韶文化(当时也称为彩陶文化)和龙山文化(当年也有称它为黑陶文化的),至于长江流域,只知道在江浙地区有些发现,还没有正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让我们十分关注的是,在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到了不同于龙山文化厚胎黑陶的细泥薄胎黑陶,同时也采集到了不同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厚胎彩陶,是胎壁薄似蛋壳的蛋壳彩陶,我们意识到这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
在天门石家河镇北水渠工程线上调查发现的一批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其聚落址之间的间距多在半华里左右,甚至有的几乎相连接,聚落遗址分布之密集,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将工程正在动工线路上的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镇北的罗家柏岭、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确定为此水利工程中的文物保护重点。这一重要发现经湖北省文化局上报国家文化部文物主管部门后,北京那边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王伯洪、张云鹏来湖北,在湖北省文化局文教科周秉全和笔者陪同下,赴石龙过江水渠正在动工的天门石家河镇北的工程段和京山屈家岭工程段了解情况,并与石龙过江水库工程指挥部联系了以上两工段暂时停工事宜。
1955年初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人员张云鹏又来湖北,对水渠工程线上考古调查确定为重点保护的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
张云鹏决定先抢救性发掘水渠工程线路上已动工的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省博物馆派笔者和程欣人参加了发掘。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动工范围的小型发掘。结束后,张云鹏马上带着我们两人转战天门石家河镇北水渠工程线上正在动工的三房湾、罗家柏岭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那个时期,湖北省水利工程遍地开花,从省级到基层,各地的水利工程工地多有文物古迹发现。湖北省文化局为趁张云鹏在鄂主持水渠工程线上天门石家河正在动工的聚落遗址考古发掘的机会,拟为湖北省基层培训一批文物考古人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石家河聚落遗址考古工作队。考古工作队由湖北省文化局工作人员、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工作者组成,其中有在北京大学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二、三期学习过考古基础知识的程欣人、高应勤、笔者和喻德智等人,还有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工作者,如在北京大学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期学习过的蓝蔚,以及省、市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和荆州专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物工作人员,还有属地京山、天门和钟祥三县的文化工作者,计30余人。考古队一边由张云鹏实地讲授田野考古理论,一边对天门石家河镇北工程段线上正在动工的罗家柏岭、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这四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小型发掘。在考古发掘的同时,张先生组织了一部分队员在石家河镇北水渠工程线所在地东河与西河之间3.5平方千米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调查发现了20余处分布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里应是一个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群。后来就将石家河镇北发现的这处分布密集的一片新石器时代遗址统称为“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1]。
到了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考古工作队队长张云鹏先生为探索长江流域原始文化面貌,对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第二次正式发掘。当时获知水利工程部门正在石家河的罗家柏岭遗址中心部位进行架设水渠渡槽的工程,罗家柏岭遗址位于东河西岸,水利工程部门为将石龙过江水渠的渠水引渡到东河对岸而建造引水渡槽。张先生得此信息后,立即带领参加发掘的笔者和程欣人等“转战”天门石家河,配合工程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发掘中发现罗家柏岭是一处大型遗址,遗迹现象复杂,当即与工程部门协商将建设渡槽部位改在了遗址南面的边缘。经过对此遗址大面积发掘揭露,发现罗家柏岭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
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于1957年下半年结束后,张云鹏先生首先整理研究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编写了《京山屈家岭》考古报告[2]。后因丹江口水库库区田野考古工作需要救急,而未能继续整理研究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资料。
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致使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中的三房湾、石板冲、贯平堰这三处抢救性考古发掘的资料,和罗家柏岭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停顿。“文革”大动乱中,已调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研究室任负责人、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主持发掘者张云鹏先生因惨遭迫害而离世。曾参加以上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笔者,当年因繁重的田野考古工作与业务及行政工作压身,没能抽出时间坐下来做积压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编写工作。直至20世纪末笔者离休后,才着手整理研究手上积压的所有考古发掘资料,先后整理编写了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的三房湾、石板冲、贯平堰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3]。接着完成了罗家柏岭等多个古文化遗址的考古简报和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
罗家柏岭史前古文化遗址,是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一处很重要的遗址,在此遗址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内,出土了一批浮雕和透雕的玉饰。其中有透雕的玉凤形环,浮雕的龙形环、人头像坠饰、人头像牌饰、蝉形饰、玉璧、管形饰、棍形饰等玉器和大量的石器(有一部分小型手工艺工具)、石料,计出土玉器40余件、石器70余件(玉、石料和半成品除外)、锥体棒形石料,以及有锉痕等加工痕迹的石器半成品500余件。在建筑遗迹内或其上的文化堆积层中,多处发现了小铜器的残片和铜绿石等遗物。出土陶片不多,其中能拼接看出陶器器形的仅30余件,约为玉、石器总数的三分之一。根据陶质生活用器的器形与纹饰判断,其应属石家河文化。根据与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陶器器形纹饰特点基本相同的季家湖类型的14C测定年代数据推断,罗家柏岭石家河文化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400年左右。
在罗家柏岭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中,为探讨此手工业作坊的性质与功能,笔者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知名学者、殷商考古学专家郑振香先生,她观察到罗家柏岭大型建筑遗迹中多为直墙、长沟、围沟、长方形土台,沟槽内壁和墙面均打磨光平,谈到1975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北发现的一处磨制玉、石器的建筑遗迹F10、F11的建筑结构中,亦有长方形、方形和拐角形的小烧土台和台阶遗迹,是地穴式或半地穴式建筑,与此建筑遗迹有许多近似之处。罗家柏岭遗迹虽是地面建筑,但其工作间亦都在地下的沟穴内。经与郑先生共同探讨后我们继续工作,从此大型建筑遗迹的结构、形制与手工业作坊遗迹内出土了许多玉器和大量石器,还发现小沙坑等遗迹,结合与罗家柏岭遗址邻近的肖家屋脊遗址发现的一批玉器瓮棺葬中均出土玉器半成品与玉料等资料分析,郑振香先生认为罗家柏岭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应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制作玉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我们一起探讨确定了罗家柏岭大型手工业作坊遗址的性质与功能,而后,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发掘报告于1994年在《考古学报》[4]上发表。
1978年,在张绪球馆长领队下,荆州地区博物馆考古人员对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的邓家湾遗址进行了一次小型发掘。1984年湖北省全省文物普查中又对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进行了普查,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所在地8平方千米范围内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0余处,确知石家河是一处大型新石器时代聚落群[5]。
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由王红星、胡雅丽、陈逢新等组成的考古发掘小组,在笔者领队下,对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的谭家岭、土城、邓家湾等遗址分别进行了小型发掘。在谭家岭遗址发掘中,发现早于屈家岭文化的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年代相当的红陶系文化遗存,即日后命名的“油子岭文化”。同时在土城城垣的夯土层内,发现早于仰韶文化的陶片,即在此之后命名的距今约7000年的边畈文化[6]。
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里的许多遗址中,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堆积层之上,同时又发现了一支晚于屈家岭文化的文化遗存。
观察这支后屈家岭文化的文化遗存的内涵,陶系仍以灰陶为主,但却是浅灰的灰白色陶生活用器,其中橙黄、橙红色陶较屈家岭文化时期有所增多。在其文化遗存的早期所含屈家岭文化因素较多,但已不见屈家岭文化代表性的双腹鼎、双腹豆、双腹碗等双腹器。早期有极少数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橙黄色蛋壳陶和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盆形宽扁铲状足鼎、深腹圈足甑、壶形器、高圈足杯、喇叭形小杯等,只是器形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器形,如釜形尖锥足鼎、锅形深腹小圜底甑、鬶、小口深腹瓮、器座等。中、晚期屈家岭文化因素逐渐减少,罐类器和大口深腹平底缸增多,增加了盆形擂钵、喇叭口筒形澄滤器、臼等食物加工器。总观这支后屈家岭文化的陶器群是鼎、甑、碗、钵、小杯、高圈足杯、盘、豆、壶形器、鬶、盆、罐、瓮、缸、擂钵、澄滤器、臼、器座等。后屈家岭文化时期出现不少玉质艺术品,生产工具中增添了一批石制小型雕刻刀等工艺工具。延续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彩陶纺轮,除仍有弧线、直线组成的图案外,又增添了太极图形的图案。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小型陶塑艺术品,在后屈家岭文化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石家河聚落群内邓家湾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小型陶塑艺术品。陶塑品绝大多数为碎块,堆积在一起,估计总数不少于万件。上万件的陶塑动物群中,有颇富动感的小人、飞禽、走兽,还有爬行动物和水生动物,其中部分属野生动物,家禽、家畜也占有一定比例[7]。后屈家岭文化陶塑艺术品中的小陶动物,不仅数量之多令人瞩目,而且种属之广亦属罕见。从这支后屈家岭文化内涵里的屈家岭文化因素,由早期多至中晚期递减,传承下来的陶器有的在器形上有些变化,可以看出它与屈家岭文化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故此个人认为这支后屈家岭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但其文化的主要内涵已有别于屈家岭文化。
这支叠压在屈家岭文化层之上、传承有屈家岭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后屈家岭文化遗存,脱胎于屈家岭文化后,在与沿着汉水支流南下的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接触和相互交流中,又融会了煤山类的龙山文化因素,是一支既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含有龙山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存。故有学者称它为“湖北龙山”,也有学者名其为“后屈家岭文化”,还有些学者各用其发掘发现后屈家岭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如在鄂西当阳季家湖遗址发现的名为“季家湖文化”,在松滋桂花树遗址发现的名为“桂花树三期”,在汉水中上游的鄂北郧县青龙泉遗址发现的名为“青龙泉三期”,发现于鄂东蕲春易家山遗址的称为“易家山文化”,同一性质的考古文化命名纷繁。鉴于其分布有一定范围,按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笔者在整理和编写以这类后屈家岭文化遗存为主的《房县七里河》考古发掘报告探讨这支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时,借苏秉琦教授“还是用‘石家河文化’为好”的看法,将这类后屈家岭文化命名为“石家河文化”。接着,在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考古工作中,发掘发现后屈家岭文化的王红星、胡雅丽同志,也撰文发表了应将后屈家岭文化命名为“石家河文化”的相同看法,从此,“石家河文化”的命名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
石家河文化向外扩张发展的分布范围,向西已至鄂西的当阳、宜都地带,其影响直抵西陵峡区;向东到达黄冈、蕲春等地,影响所及已至江西修水一带;向南到达湖南境内的澧水流域;迤北沿着汉水流域向中上游的鄂西北郧阳地区扩展,直达豫西南的镇平、淅川一带,淅川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期石家河文化;在这一地带的河南煤山龙山文化一、二期中,出土陶器中有小型罐形铲状足鼎、漏斗形澄滤器、高圈足杯、喇叭形小杯、陶塑红陶小动物中的长尾鸟等一批石家河文化特色的遗物,说明石家河文化的传播已达豫西南地带,其影响所及直至豫中地区。石家河文化在与周边同期考古学文化交流融会中不断丰富自己,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地域类型。石家河文化定名后,随之将季家湖文化、青龙泉三期等各区域同一性质的考古学文化,统一归入石家河文化范畴。
根据肖家屋脊遗址和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遗址测定的14C年代数据,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4200年,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绝对年代基本相当。
1987年上半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荆州博物馆联合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的邓家湾遗址进行了一次小型考古发掘,又有了一些新收获[8]。
1989年5月,在中国考古学会于长沙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找到笔者,谈及拟对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址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了解的设想,我欣然表示支持,会议结束后便陪同严先生赴天门、京山县看了石家河、屈家岭遗址。当年下半年,由北京大学、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在石家河成立联合考古队,起初严先生任总队长,委任笔者和张绪球为副队长,发掘工作开展一段时间后,为有利于实际工作,笔者将副队长职务交给笔者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权喜同志担任。此次发掘分工是,北京大学和湖北省博物馆负责发掘石家河聚落群中的邓家湾遗址,荆州博物馆负责发掘肖家屋脊遗址。
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联合考古工作,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于1991年先后结束发掘,接着分头进入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
199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石家河联合考古队副队长的杨权喜同志领队,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的邓家湾遗址进行补充发掘,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大型城址,从城址的层位叠压关系看,城址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使用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邓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仅占城址西北角的一角之地,此城址之大已可窥见一斑。
严文明先生在指导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大型考古发掘中,以重点发掘与聚落群的全面考古调查相结合,对聚落群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查了解。1990~1991年,严文明先生派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赵辉和张弛对在石家河聚落群8平方千米范围内的城址和密集分布的40余处古文化遗址的文化遗存逐个地进行了勘查。经勘查得知,城址平面呈近方形,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史前城址如此之大,大得惊人,以发现地将其命名为“石家河古城”,在完成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的田野勘查任务后,当即写出了考古调查报告。
考古调查发掘获知,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内的原始文化序列是,距今6000多年(与仰韶文化年代相当)的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三房湾文化(有称为后石家河文化者),其中文化遗存则以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为主,而以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最多,文化堆积最厚。这表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的先民在此居住的时间最长[9]。
1992年以后,石家河联合考古队先后完成了石家河聚落群中肖家屋脊和邓家湾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10]。
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石家河聚落群中发现的石家河城址的城垣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小型发掘。发掘选择在古城址东南的底部位置,解剖残城垣发现夯层,揭示厚薄不等的夯土堆积层残存7层。残城垣呈东北—西南走向,与三房湾遗址南部城址的南垣相接,东侧经过蓄树岭遗址的南部与黄金岭遗址处的东城垣相连。至此,石家河古城除东北部被土城遗址打破外,其余城垣范围基本确认[11]。
解剖城垣,从夯层中的出土遗物获知,古城兴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叠压在城垣之上的文化层共分12层,其中的灰沟、灰坑、灰烬层、墓葬等遗迹内的出土遗物均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可知此时的古城址已是废弃期。此结论与1992年解剖古城西北部邓家湾一带城垣所得相对年代的认识大体一致,应该说基本上反映了石家河古城的兴废年代。
石家河聚落内现存大、小两座古城城址。大城是两湖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城址中最大的一座。大城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1100米,城内面积约132万平方米,可使用面积为120万平方米左右。城址带环形城壕的面积则达180万平方米。西、南两面城垣保存较好,残垣顶面宽8~10米,底部宽约50米,现存城垣残高6~8米,城垣外侧环绕的一周城壕均为人工开挖,周长约4800米,壕面宽80~100米。此城址之大,实为史前文化城址中所罕见。
打破大城城垣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城址,当地名之为“土城”,此城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510米,东西最宽处为280米,土城城垣顶面宽4~6米,底部宽10~28米,其东段偏北处有一宽12米左右的豁口,可能是城门遗迹[12]。
考古发掘获知,大城与小城的建筑年代有先有后,大城建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小城建于石家河文化时期,但都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晚期。
大城的城垣上一直未发现城门豁口遗迹。大城与小城的性质和用途,尤其是大城的性质和作用引人思考,看法不一。我们的观点是:“按照恩格斯所说,城垣的出现代表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石家河古城是军事用途,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屈家岭文化早、中期至晚期,长江中游古城址出现10多处,不是偶然现象。古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经过考证都认为,屈家岭文化是三苗族创建的文化,屈家岭文化时期,正是古史传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之时,故长江中游江汉地区此时城垣高筑、古城林立。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石家河古城所处时代,贫富分化并不明显,阶级差别不算太大,城垣首先是出于防洪的需要而产生的”[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看来,石家河古城中的大城与小城的性质和用途,有待继续探讨。
2011年3~4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大城城址内进行小规模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收获。在大城的城垣下发现一条南北向的古河道,城垣第6层下发现木构遗迹打破河道淤泥层。其中北侧一排共6根木柱,3根为方木,3根为圆木;南侧一排共5根木柱,其中1根为方木,4根为圆木。木柱直径一般在0.04~0.11米,因淤泥层堆积厚而未清理到底,木柱长度不详。“根据石家河古城内的地形地貌及淤泥堆积的特点分析,在没有形成城垣以前,这里存在一条通往湖泊的南北向古河道,而木构遗迹的位置刚好垂直于古河道,可能是连接三房湾遗址与蓄树岭遗址的一处古桥遗迹。”木构遗迹的年代,应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晚期[14]。
谭家岭遗址南部邻近三房湾遗址的低洼地,开挖的探方内文化堆积层共分9层,其中第3~6层出土的陶器属石家河文化晚期,第7、8层出土的陶器、石器属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第9层为黑色淤泥堆积,厚度超过1.2米,因地下水位过高而未能发掘到底,出土遗物除较多的泥质磨光黑陶外,还发现大量的木质遗物,圆木、方木、木板、木制舟形器、竹编织物、树叶、芦苇、田螺等;随后,在古河道内的屈家岭文化层和石家河文化层遗物中,又新发现了一批有刻划符号的器座、双环耳小杯等陶器。从出土遗物分析,谭家岭遗址与三房湾遗址之间存在一条东西向的古河道,大约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古河道淤积成为低洼地[15]。
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晚期,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中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都是新石器时代的尾闾,是原始社会解体的表象。屈家岭文化晚期城堡的出现,特别是以城垣、城壕、土台组成的石家河古城浩大工程的出现,标志着氏族内部此时已产生了拥有权力的权贵。修建城池不是一两个人说干就能干成的,如果没有经济权力的行使,伴随着意识形态权力(宗教作用和武力征服行为)的行使—即执掌社会权力的权威首领,进行耗费如此浩大公共劳动的工程应当是不可能的。此时期,以大、小城先后为中心和周边聚落群为依托形成的,一个以城邑为中心的阶层划分现象已经出现,石家河聚落群似已处于以神权为中心的部落酋长制时代,即已处于国家文明的前夜。
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汉地区的缩影。石家河新石器时代聚落群内的罗家柏岭遗址发现5件小型铜工具残片、铜矿石、锈蚀的铜渣和一批浮雕与透雕的精美玉器。有关专家经对石家河文化玉器观察研究断定,石家河文化玉器,是使用金属加工工具“砣”制作的[16]。在邓家湾遗址发现了铜片和少量铜矿石,在肖家屋脊遗址也发现了铜矿石碎末。这些重要发现亦预示着江汉地区即将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青铜时代即将来临。
注释
[1]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天门市石家河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10),地质出版社,1996年。
[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5]荆州博物馆内部资料。
[6]湖北省博物馆内部资料。
[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王劲:《浅议石家河文化陶塑艺术》,《华夏考古》2011年第4期。
[8]荆州博物馆内部资料。
[9]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10]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荆州地区博物馆等:《天门邓家湾遗址1987年春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
[11]孟华平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掘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7日。
[12]刘森淼:《荆楚古城风貌》,武汉出版社,2012年。
[13]王红星:《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考古》2003年第9期。
[1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三房湾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
[15]孟华平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发掘取得新进展》确认石家河古城东南部存在城垣堆积,《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7日。
[16]20世纪70年代,浙江省博物馆玉器专家牟永抗先生应邀来湖北鉴定相关玉器。
编者注
文中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考古工作队队长张云鹏……”,其年张云鹏任职有误,详见本书《张云鹏考古年谱》。
相关王劲先生考古文存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