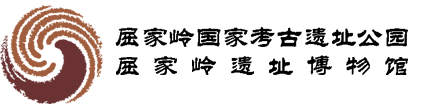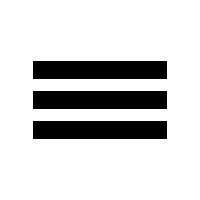三苗故土
金秋时节,正在火热建设和完善中冲刺挂牌评定工作的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古稻田区种植的粳稻泛起一片片金色的波浪。站在北面遗址核心区放眼四望,一定会让你沉醉于五千年来渊源流长的稻香之中。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位于中国农谷核心区·屈家岭管理区屈岭村和京山市雁门口镇高墩村。遗址总面积达2.84平方公里,是以屈家岭遗址点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九亩堰、土地山和杨湾等遗址点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环壕聚落。屈家岭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存在于长江中游的一种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自身有连续发展序列的文化系统,被认为是打破中华文明“黄河一元论”的实证,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越来越显现其夺目的光芒。
三苗由来
创造屈家岭文化的先民是三苗人。三苗的活动范围据《战国策·魏策一》载:“昔三苗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屈家岭文化主要由距今约5900-5100年的油子岭文化发展而来,分布范围西至长江三峡,东至鄂东,北至河南伏牛山麓,南至湖南洞庭湖与江西鄱阳湖之间。屈家岭文化孕育了距今约4500-4200年的石家河文化。考古学界与民族学界一直把屈家岭文化作为研究三苗部落集团及其文化来源的对象。
有关三苗的来源,学术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外来说:这一观点认为三苗来自九黎。传说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华夏部落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其中相当一部分部落成员向南退却,在江淮、江汉和洞庭湖之间生息繁衍,与原来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新的部落集团,也形成了新的“三苗文化”。一种是土著说:这一观点认为,三苗原来就是居住在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九黎并不是三苗的主源。不管怎么说,这一族群毫无疑问在屈家岭文化涵盖的这一片土地上稳定繁衍生息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史前农业定居社会一段文明的缔造者。三苗部落集团纵跨三省,这个庞大的族群何去何从,是否曾经建立了萌芽性质的国度,从愈来愈引起世人惊奇的天门石家河遗址和2018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沙洋城河遗址等屈家岭文化遗存来看,似乎可以窥见一斑。相信考古研究专家们默默辛苦的付出,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三苗“稻”理
宜稻乐土,安居福地。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研究的不断深入,江汉平原北部汉水以东地区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高度繁荣、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地区,不容怀疑。山峦起伏的大洪山南麓太子山下,青木河与青木垱河两条古河流分别发源于山系西北和东北,夹成中间一片丘陵山地呈菱形地块,这里便是屈家岭遗址核心区,地理坐标30°50′13〃N,112°54′14〃E,遗址地貌属于丘陵岗地,其北面是太子山主峰上的白龙观。为了进一步揭开屈家岭遗址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并下达计划,目前正在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据正在这里潜心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屈家岭工作队队长陶洋和副队长张德伟两位同志介绍,这里三面环山,向南是典型山前平原,周边沟渠纵横,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较多,水热条件和暖湿气候十分适合水稻生长,且生产、生活用水方便,受洪水影响较小。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显示,屈家岭遗址实为以稻作农业为定居发展前提的一块福地,足见先民智慧。
磨石为稻作之利器。走进已经试运行的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当你看见一些貌似简单的石斧、石镰、石锄、石锛、石凿等生产、生活工具,可别不以为然。正是这些先打制、后精心磨制的石器,成为先民们较大规模开垦种植水稻的功臣。较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工具显然要更先进些,一件比较精致的石器,往往要经过打制(有的需要开料)、琢平、磨光等工序,有的还要钻孔甚至抛光。大多数石器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琢磨,而磨成能够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工具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古人所谓“铁棒磨成针”的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屈家岭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技术虽然并不存在新的突破,但集中反映了当时大型甚至特大型聚落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情形。当然,聚落先民们还使用了木器、骨器等其它生产生活工具。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先进生产生活工具,开启了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史前农耕文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田”纹陶球娓娓“稻”来。说“田”纹陶球是屈家岭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人可能会嗤之一笑,那是因为他(她)还不知这枚陶球上浓缩地反映出史前先民们的种稻规模和管理水平。在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块较大的红烧土里面夹杂着大量的稻壳。1956年仅发掘858平方米,就发现一片面积约500多平方米、体积约200立方米的烧土遗迹。这些烧土是由泥土掺和稻壳和稻的茎叶做成的,上下密结两层。以后的发掘中,这样的红烧土比比皆是。“田”字纹陶球一是反映了当时水稻种植面积之大,二是反映了当时农田的规模化、整齐化和排灌管理技术的成熟。试想想,当时的屈家岭遗址作为一个大型的聚落群,相对较多的人口集中住在一起,主要靠什么生活呢?如果原始农业不发达,过分地依赖渔猎是不行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靠比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水稻种植为主。“田”纹陶球间接反映了长江中游汉水之东的屈家岭遗址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从汉字文化发展的渊源来讲,此陶球上的“田”形纹饰,看上去比商周时期甲骨文上的象形文字萌芽更早。
“粳”稻香飘五千年。屈家岭文化的稻作遗存最早发现于屈家岭遗址,也是长江中游第一次发现史前稻作遗存。当时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对1956年发掘出来的一些谷壳进行了鉴定,结论是:“……这些谷粒当属粳稻,且在我国是比较大粒的粳型品种。”据姚凌、陶洋、张德伟、罗运兵等人在《江汉考古》2019年6期发布的《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一文称,通过对完整炭化稻的长度平均值及长宽比进行测量,发现油子岭文化时期炭化稻的长度平均值为4.58毫米,长宽比1.53-2.12;屈家岭文化时期炭化稻的长度平均值为4.75毫米,长宽比1.59-2.07;石家河文化时期炭化稻的长度平均值为4.8毫米,长宽比1.72-1.99。按照目前粳稻与籼稻的长宽比判别标准,一般粳稻的长宽比小于2.3。从屈家岭炭化稻的尺寸比例来看,其应属于粳稻类型。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全世界的稻属植物中,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种,栽培种仅两个。亚洲栽培稻又名普通栽培稻是其中一种,可能源于本地多年生普通野生稻,而普通野生稻也存在籼粳分化,在遗传上是异源的,从驯化到栽培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资料表明,“屈家岭遗址自油子岭文化早期有人类定居开始,就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稻作农业。……在此之后,北方的粟作农业传播至此,并未对稻作农业的主体地位产生影响。”(《江汉考古》2019年6期)稻作由南向北传至这里,再通过屈家岭文化的强势影响到仰韶文化的部分区域,都有遗存实证。屈家岭遗址作为屈家岭文化极具代表性的遗址,其遗存表明稻作占据了当时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反映了原始农业集约化程度。这也说明,江汉平原乃至更大范围的长江中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核心,“两湖熟,天下足”之说具有史前依据,在中华文明古国的形成和繁荣发展中显现出其战略性的作用和地位。
三苗陶梦
屈家岭文化时期革命性的制陶成就在于普遍使用快轮制陶,陶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泥质陶器主要有食器、水器和容器等;夹砂陶器主要是蒸煮器。从颜色上讲,一般以灰色为主,黑色次之,红色占第三位。屈家岭遗址内出土的陶器有彩陶杯、彩陶碗、双腹鼎、筒形器及甑、罐、锅、缸等等数不胜数。彩陶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这里专门说说屈家岭遗址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类彩陶:
匠心独运蛋壳彩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便与屈家岭遗址结下不解之缘的考古专家王劲先生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中说,“薄如蛋壳的彩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高度水平,是屈家岭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蛋壳彩陶胎仅0.1-0.2厘米厚,器型有碗和杯两种。橙黄地,施黑色、橙红色陶衣,绘红、黑彩,或二色兼绘,造型美观。蛋壳彩陶杯斜壁平底似喇叭状,用卵点、叶形、方框等组成的花纹彩绘于器外,少数内外都绘彩。”张绪球先生在著述的《屈家岭文化》一书中称,“屈家岭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共发现蛋壳彩陶片八千二百七十五片。”现在看来,该遗址点仅为弹丸之地,却见蛋壳彩陶之多。现今出土的一些蛋壳彩陶杯内,经淀粉粒分析,杯内壁发现了可能跟酒的发酵相关的线索。据专家推测,如此之薄的蛋壳彩陶器一般用作礼仪祭祀之用。这同时反映出,当时稻作农业之发达,人口虽然增多,但仍有余粮用来酿酒,表明当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专业化的陶工才得以一门心思发挥自己高超的制陶、绘彩技艺和个人天赋,从而使首先满足实用之需的陶器不断融入了他们记录自然、征服自然的集体智慧和美好愿景,因而显现不可磨灭的原始艺术价值。
纺纱织衣玩转彩陶纺轮。到过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人,或者通过宣传视频,一定会对博物馆南面的一个带圆型水池的广场感到惊奇。没错,那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广场,那是根据屈家岭遗址出土的标志性文物——双鱼彩陶纺轮建立的纺轮广场。屈家岭遗址内发现了大量纺轮,其中尤以彩陶纺轮最具特色。这种彩陶纺轮均为火候较高的黄色陶质,一般先在两面涂抹橙色陶衣,再在单面绘饰以褐色(或红色)的漩涡纹、直线纹、麻点纹、同心弧线纹、双鱼纹等等。这些图案的线条以各种方式通过轴心,来表达各种旋转的视觉形象。那么,这些小小的彩陶纺轮到底作什么用呢?顾名思义,当然是纺纱之用。屈家岭文化以前,流行大而厚重的纺轮,转动惯量大,适用于纺粗硬的纤维,成纱较粗。屈家岭文化时期,纺轮由重变轻,由大变小,因此纺出的是更细的纱,织出的是更薄更密的布,反映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和纺织手工业的大发展。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纺轮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特别,纹饰丰富,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无限的想象。张绪球先生说,“彩陶纺轮的花纹大多与旋转有关,当纺轮转动时,这些花纹能随之产生一种快速的动感,它不仅可以增加美感,消除疲劳,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希望纺轮快转动、多纺好纱的理想和追求。”更有学者在对我国古代历史进行综合而又深入研究之后大胆认为,这些“纺轮的数量显然超出常规用量。也就是说,它不是日用的纺轮,而是原始宗教的法器。”(庞朴《谈玄》,《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这一说法新颖,有一定合理性。古人对天体向来崇拜,人类自诞生那天起,日月星辰的运行、变幻无穷的气象,无不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屈家岭彩陶纺轮图案都是对旋转物体的具体描绘,似乎已超出装饰彩陶纺轮的审美情趣,而成了崇拜,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含义。纺轮通过旋转可以把葛麻变为细线,从而制成各种衣物,它与制陶用的转轮都有造化万物的功能,于是古人就把它装饰以特殊的图案,来作祭祀天地用的法器。更有甚者,有人推测屈家岭遗址出土的彩陶纺轮是玉壁或古铜钱的前身也未为可知。再说双鱼彩陶纺轮,一说此为最早的太极图案。史前先民对天地、水流,对鱼类等自然现象和生物种类都有一种寄托愿望性的崇拜。一方面,因为天圆地方,水生万物,鱼多子,麻点纹代表天象或者稻米等等,都未为可知,一些有代表性纹饰的陶器成为一种图腾用作祭拜祖先和通天地的语言表达,从宗教的起源和产生来讲,并不神秘。如前蛋壳彩陶所述,同样,屈家岭遗址上如此众多的彩陶纺轮,不仅代表了古人认识自然、掌控自然、崇拜自然、希望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浪漫主义思想,也开启了我们研究原始宗教和艺术产生的思路,帮我们界定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水平。一枚小小的彩陶纺轮,可能还暗藏或者浓缩了史前先民们的宇宙观。
稻盛陶兴话古今。总之,在这一块典型的南方文化乐土上,曾经生活在屈家岭遗址上的三苗族群先民们因地制宜筑起最坚固安全的大环壕,吃的是当时最优的粳稻米,穿的是最细致紧密的衣服,住的是结实又防潮的红烧土房,安居而乐业。长江中游江汉地区农耕文明的兴起并强势扩张和影响周边广大地区,无不显现屈家岭遗址在新石器晚期独特的历史、科学、文化价值。
“稻”意今何在,且看遗址粳稻今又熟。陶梦今何觅,还看屈陶·屈窑“黑陶”飞重洋。近些年来,落户屈家岭这块热土上的湖北屈陶屈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系列黑陶产品活色生香,远销海内外。目前,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火热的旅游攻略是,以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发散点形成一线串珠的环线或区块,向南是青木河沿岸,向西经工业园区的湖北屈陶屈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可往月宝山万亩桃园,向北农谷大道经月湖公园、普云禅寺和独有一种秀美的美丽乡村梭墩村可再往王莽洞、虎爪山等景点。朋友,或许你我皆为三苗后裔,即便不是,要知道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棵枝繁叶茂又根深的大树,屹立东方,影响和地位强者恒强。你若有意来探祖寻根,领略屈家岭文化博大的精髓,开馆之日,欢迎你走进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到本地饱览生态宜居的美丽风光。(作者: 周丽 赵媛彦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