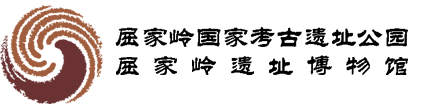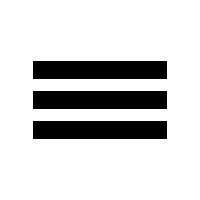“巨锅”群英会

锅,金旁,异体字之一“鬲”,许慎《说文解字》中曰其秦名土釜,今俗作锅。土釜者,出於匋也,读若过。锅之实物一般圆形中凹,对现今的我们来说,当然是一种常见的烹饪器具。民以食为天,自从远古先民掌握运用了“火”,再通过“锅”进行熟食革命,善待了人类的肠胃,人类体质无疑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大大促进了生命的进化,也让人类不断走向了更高阶段的文明,可谓具有划时代意义。
那么,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遗址上的三苗先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锅呢?在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当我们从众多的石器、陶器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中,近距离看见独立展柜内一口巨型陶锅,一定会蓦然产生一种神奇的穿越感——仿佛五千年前创造屈家岭文化的三苗先民们近在眼前,正围着这口锅大快朵颐地享用着他们的美食哩!
据张云鹏先生编写的《京山屈家岭》一书报告描述,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这一口巨型陶锅,属屈家岭文化时期,粗泥陶质,较软,胎色褐黄,含有大量碎陶末。器型与现在的大铁锅相同。长唇外侈,壁上部作弧形内凹,中部有凸起的附加堆纹,下部内收构成圜底,底部下突呈乳头状。口沿满饰双人字形划纹,壁中部附加堆纹为格形纹。手制。高33厘米,口径86厘米,厚1.83厘米,容量为0.65立方米。
五千多年前,这口锅是用来烹煮食物的吗?煮食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大量人工栽培种植、至今仍为优良品种的粳稻米?煮食那个时期已被先民们驯养的猪、鸡等家禽家畜?抑或聚落先民们用箭簇等工具捕获回来的各种动物?还有先民们用自制的网具到青木河里捕捉回来的鱼儿?有资深考古专家在分析比较我国同时期不同史前遗址出土的类似遗存后,不由惊叹其为“天下第一锅”。不言而喻,这当然是一个大团结式的炊煮器具。试想,在史前那样一个时代,屈家岭遗址上的三苗先民们仅凭磨制的石器、兼有少量木器和骨器,便开创了一段堪称同时期典范的农业文明。这一口大陶锅随之出现,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不能不令人遐想连篇。
那么,按图索骥,或者睹物思人,我们不禁要问:何人才能掌管、使用这一巨型陶锅呢?多少人可以同时享用这口大锅所煮的食物?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用上这么一口大锅来烹煮食物?根据其出土情况,专家们研究推测,这口锅不太可能作冥器之用,应该是屈家岭遗址远古时代食物充足、社会繁荣、聚落强势的一种象征。此陶锅的用途或许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形:
中心部落最高首领召集会议待客之用。屈家岭遗址之所以成为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以其先进的稻作农业和和独具特色的制陶业最富盛名。陶器的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的发达。成熟的农业社会可以稳定地解决大量人口的温饱问题。毋容置疑,已经定居在屈家岭遗址上的三苗先民们,其食物主要以稻米为主、粟米为辅,同时有少量饲养的家畜、家禽和采集狩猎所获作为食物来源补充。在盘点2015年以来考古收获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家岭遗址联合考古队副队长张德伟介绍,2020年在屈家岭遗址点南部台地保护大棚发掘区内,揭露了屈家岭文化时期两座平面结构均为3间的大型长方型房屋建筑F15和F18,同时还发现了可能属于F18的附属仓储类建筑F17。建筑遗迹F15的3连间房屋面积分别为20平米、25平米和15平米,由外围柱坑合围的总面积约160平方米;建筑遗迹F18的3连间房屋面积分别为14平米、14平米、25平米,由廊道等附属设施围合的总面积约80平方米。有专家认为,这种住屋的空间布局,隐含着一种制度性的结构,居住在房屋内的人可能是一个亲族团体,代表着一个大的家庭。这种亲族团体往往代表着聚落很强的凝聚力,换一句话说,很可能是部落首领或者权贵家庭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一般先民家庭尚且能够居住在这样的房屋内,部落首领或者权贵家族的住房应为更高等级。由此,大锅会不会作为部落首领大家庭日常私用呢?好象不太可能。撰写《屈家岭文化》一书的作者张绪球先生前几年在接受《荆门日报》采访时说,“这些大型陶器在成型和烧制方面都是很困难的,需要有成熟的经验才能做好。这么大的锅,肯定不是日常生活的炊具,因为用这种大锅做饭,一次可供几十人用餐。”屈家岭遗址是一个以屈家岭遗址点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杨湾、土地山、毛岭、大禾场、九亩堰等十二处遗址点在内的新石器时代大型环壕聚落遗址群,在青木河与青木垱河中间及两岸,这些遗址点相对分散,且功能分布上已经出现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中心聚落的头领定期不定期召集“中层干部”以上的会议,安排生产,商议大事、急事,就会用上这口大锅招待大小首领。这一方面说明定居农业的发达保证了先民们食物的充足,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结构出现权力集中、社会阶层分化,同时还有物资分配的不均等现象。
中心聚落大型生产劳动时公共烹煮之用。屈家岭遗址多年的考古,揭露了距今约5900年的油子岭文化时期至距今约4200年的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多处居住类遗存,专家们结合房址规模与布局判断,这片土地上有史前先民们的一般居住区,也有中心聚落的居住区。连间房F18旁边发现了可能的粮仓F17,F15连间房东部还揭露了一处小型室外广场类设施(红烧土类遗迹),总面积约120平方米。这说明屈家岭遗址上的先民们以成熟的技术大规模种稻谷,促进了人口的发达和人体素质的增强。反过来,以人作为唯一主体的生产力之发达,又更加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大量的余粮保存下来,社会出现分工,便会出现权力统领与组织协调,便会有规模化的聚集性公共活动。不难想象,在五千年以前,靠天吃饭种地的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必定积累了一定的农事经验并掌握了一些气候、天象规律,尽管是磨制的生产工具,但毕竟使用的是石器,集中精壮劳力抢种、抢收是必不可少的;修筑既能排灌又能防御的大型环壕或者水利沟渠等,需要组织大量劳力非一朝一夕投入工事中;修建那个时候的红烧土房(也可看作是那个时候的“水泥”地面、“水泥”墙体,因为埋于地底保持了五千年尚未分化,堪比水泥结实)也需要很多人分工配合。等等情形,都是使力气或者有技术的能人集中突击性干活,必定都会用上这口大陶锅供多人同时吃饭。这种亲近又团结的方式,便逐渐形成一种中心聚落与附属聚落的层级关系,也强化了部落首领的权威,由此便出现了史前社会早期政治的萌芽形态。归“口”管理一词,可不是后人凭空捏造。
中心聚落神秘的祭祀之用。旅加学者廖平原先生在谈到世界文明起源的多元化时认为,定居生产的农耕文明是一种集中复杂化的成熟文明。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只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聚居才能构成从量变到质变的文明转化。湖南洞庭湖平原与湖北江汉平原很可能就是文明发源地。屈家岭文化显然不是初始状态,而是成熟状态。从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展陈的筒形器、四耳器等大量器物来看,屈家岭遗址自距今约5900年的油子岭文化时期,无疑已经出现了有先民精神信仰的祭祀活动。考古专家们分析判断得出与学术界完全一致的意见:它们只能是屈家岭原始宗教活动的遗物。筒形器被认为是一种巨型陶祖,欢庆丰收时,或者选定的吉日,在神秘的祭祀活动中,人们有组织地大量聚集在一起,按照一种隆重的仪式进行祭祀,意在通灵天地四方,乞求祖先赐福免灾,保佑部落子孙繁衍、族群兴旺。那么,他们饲养的家猪或者捕获回来的其它大型动物,就有可能作为最好的礼物放进如此巨大的陶锅里,摆在祭台上敬奉给祖先和神灵。祭祀结束后,人们架起这口大陶锅,燃起熊熊的火焰烹煮大量的食物。祭祀之后,留下来进餐的至少是聚落的大小头领与一些生产劳动能手和能征善战的精英。盛大的活动,盛大的聚会,他们围着这口大陶锅,一边享用美酒美食,一边载歌载舞,从而激发出一种共同的精神力量,不断地将屈家岭遗址的繁荣兴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
中心聚落非比寻常的会盟待客之用。屈家岭文化时期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鼎盛时期。长江中游、汉水之东的屈家岭遗址所在地,当一个史前大型聚落遗址群发展到经常以遗址核心区为中心产生一些聚会,还可能与强势扩张后不同文化圈异族部落头领间相互交往、物物交换、文化交流有关。有专家根据黄河流域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的特点和遗存性质内涵并结合地理条件分析,认为屈家岭文化向北渐渐扩张有一个基本明晰的线路图:首先由屈家岭文化中心分布区即江汉平原的屈家岭一带,越过大洪山、荆山向北通过“随枣走廊”到达随州、枣阳地区,沿汉水向上到达宜城、襄阳、房县一带的鄂北地区,向东到达大别山脚下的麻城、罗田一线,这就打开了由江汉平原通向南阳盆地的缺口,屈家岭文化便以不可阻挡之势挺进到豫西南地区,其势力占据该地以后,就打开了向中原、关中传播的大门,进而向北到洛阳、郑州一带的伊洛地区和黄河中游的两岸。另一方面,屈家岭文化到达以前的上述地区,本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也是北方华夏部落集团的势力范围。中原华夏集团文化在南下的过程中,势必与三苗集团文化产生矛盾。据大量史记性文字资料反映,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战事交锋可谓势均力敌、旷日持久,两个集团在不断碰撞的形势下,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也在加快进行。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一个代表性遗址,处于两个文化集团南北交汇地带,无论是各路英雄征战出发前聚集领命听令,还是北方文化集团邻近的聚落头领带队前来进行谈判或物质文化交流,这一口巨型陶锅都可能是一种为征战将领壮行或者接纳四方宾客来此会盟的历史见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于2020年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70年来的考古研究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段时期足以和当时的黄河流域、长江下游文化媲美,这就是距今53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主导完成了长江中游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实现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 空前统一和繁荣。它西入关中,北进河洛,挺进淮河,为史前中国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总之,这可是一口不同寻常的陶锅。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内目前展陈的这口锅只是复制品,真品早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足见其稀罕,足显其价值之宝贵!(通讯员 周丽 陈志华 李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