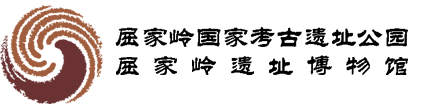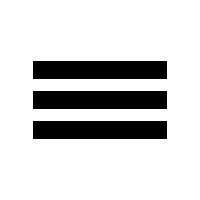往事“钺”千年——屈家岭遗址宝物探秘
源远农魂五千年,三苗聚落“钺”应知。每一件文物都是不可再得的历史语言,承载着它所处年代地域内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历史信息。在屈家岭遗址博物馆,有一件“玉钺”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有幸去一睹其玉“容”的人,可别以为它是沉默的。万物皆有灵,这句话往深刻里讲并不是无稽之谈,也并不是唯心之说。无论是被深埋地下,还是被陈列在独立展柜里,其实它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史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有关三苗先民的故事,只是我们还没有读懂它的特殊语言罢了。农耕?征战?会盟?祭祀?这件“ 玉钺”无疑是史前屈家岭遗址上的三苗先民们创造屈家岭文化的一段历史见证,本文就此先作一些推测性浅析,期待各路专家学者前来探秘解疑。

建设中的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景
“玉钺”何物?
先从“石钺”说起。钺,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石制品之一,见于大江南北的许多遗址之中。钺的最初形状和名称是斧。许慎《说文解字》曰:“戉,大斧也。”段注:“俗多金旁,作钺。”根据考古专家们已有的研究进行综合归纳,钺以扁平、穿孔、双面刃为主要形态特征,而且在装柄方式或钻孔位置方面与斧、铲等生产工具有所区别。从国内各大遗址出土的斧钺类实物形制来看,钺较斧宽阔,一般比较扁薄,近上端有一圆形穿孔或有上下并列两孔,以供系缚时捆扎之用。

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展陈玉钺A面
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遗址成为长江中游农业文明的典范,其生产工具以石器发现最多,而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斧,都是双面刃。《屈家岭文化》的著述者张绪球先生在该书中介绍,屈家岭文化出土的斧可分实用性和礼仪性两种。一种石斧上窄下宽,呈梯形,一般以中小型为主,多出于屈家岭文化年代较晚的遗存中。这种礼仪性石斧也称作“钺”,顶端略窄于刃端,双面弧刃,形体扁薄,通体磨光,上端有对钻的圆孔。
再来说说这件“玉钺”。玉是山川的精英,比较稀罕和少见。从硬度上讲,玉分为硬玉和软玉。硬度标准采用的是矿物学或宝石学中表示矿物硬度的一种标准,范围一般在1—10之间。软玉硬度一般为6.0-6.5 ;硬玉的硬度一般为6.5~7。以玉石材料加工成玉钺,需要使用比玉类硬度更大的加工工具和先进的加工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先不说其用途,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据了解,我国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文化中就出现了线切割琢玉工艺,这说明中国史前先民已经掌握了当时的高科技技术,故能加工出精美的玉钺等玉类产品。

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展陈玉钺B面
屈家岭遗址发现的这件玉钺,呈梯形,上窄下宽,双面刃,上部有一圆孔,孔径一面大,一面小,为对钻形成,玉钺一边有未加工好的凹凸不平的自然面,通体磨制精细,为深绿色青玉,长8.9厘米、上宽6.15厘米、刃宽7.9厘米、厚1厘米、孔径1.1厘米。旅加学者廖平原先生认为,人类的历史发展应该是先有了基本的文明,然后才有相应的文化产生和发展。文化可以说是文明的映射和层次。中国多元一体的原生文明中,一定少不了长江流域。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汉水之东的屈家岭遗址具有成为中国史前农业文明典范的得天独厚条件,屈家岭文化显然不是初始状态,而是成熟状态。玉钺是石斧的迭代和高级版本。
那么,我们根据廖平原先生的观点,可以推测出这件玉钺应该是屈家岭遗址作为长江中游史前农业文明典范的一种映射。从石钺到玉钺的出现,单从器质来讲,这应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屈家岭遗址上三苗先民们生产、生活迈向更高文明层次的一种历史性见证。
玉钺何用?

遗址公园内青木河亲水码头
据了解,我国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早期之钺,大多以石为之,而且分布范围较广。考古专家们和人类学专家对我国大量的史前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研究表明, 钺在我国史前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从石钺到玉钺其功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作砍辟生产工具之用;二是作近距离交战武器之用;三是作为社会阶层权力的象征和墓葬、祭祀礼器之用。前两种情形多为石钺,后一种情形中便出现了玉钺。
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可以获取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农业在这一生存的困境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在史前农业定居社会,人们较多数量地制造并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石钺等重要工具,是一种集体行为,有秩序的行为。屈家岭文化的稻作遗存最早发现于屈家岭遗址,这也是长江中游第一次发现史前稻作遗存。并且,屈家岭遗址近年还发现了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长江中游最早的炭化粟作遗存,可见屈家岭遗址史前的农业结构是以稻为主、粟为辅的水旱兼作模式,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农业文明的典范。屈家岭遗址的三苗先民们在开荒、垦田和建筑房屋过程中一定少不了使用石钺这种砍辟功效很大的生产工具。
一般认为,屈家岭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汉水之东的史前文化遗址,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其序列依次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根据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研究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在撰写的《长江中游史前石钺的功能和社会意义》一文中说,大溪文化早中期及更早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已出现一批玉石钺。至大溪文化晚期,钺的使用现象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的周缘区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进入了空前的统一繁荣阶段,在屈家岭文化的核心分布范围内,钺多见于城址和中心聚落之中,暗示了钺与聚落规模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彭小军还说,“距今5300年前后,伴随着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的动荡和整合,大量的钺被投入关隘性区域和文化接触地带,它们很多被普通‘战士’所持有,充当近战武器的职能。”屈家岭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存续的一种强势文化,基本横贯整个湖北省东西,纵跨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在以核心分布区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必定要大量使用到这种具有很大威力的近距离交战武器。
再说由石钺发展而来的玉钺,应该体现了从实用到抽象的变化过程,也体现了史前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学者认为,中国在青铜器时代之前出现了玉器时代。早期玉器的社会功能演变或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玉钺作为上层社会或贵族拥有的特殊产品,已被赋予军权或者王权的专属礼仪化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史前农业社会中,农作物的生长有规律和周期,靠天吃饭的人们慢慢会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有所敬畏,感到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每当风调雨顺,抑或遭遇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或者目睹生老病死、日月交替、季节变幻,人们便想到了祭拜祖先和神明,钺作为礼器之一便产生了。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发现多件带柄的玉钺以后,人们知道这种在遗址中出土不多、制作又特别精致美观的斧已经不大可能用于农事,极有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用具。有研究发现,玉钺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已完全丧失了作为生产工具或武器的功能,变成了一种高级的礼仪器物,即权力的象征。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多次考古发掘已经探明,屈家岭遗址作为屈家岭文化的命名地,是谛造了长江中游远古农业文明的一个大型聚落群。遗址核心区由南而北分别是陶器手工作坊区、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廖平原先生在表明他的“文明”观点时说,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展陈的这件玉钺看上去就像一个“且”字。“且”字可能就来源于石斧,是一种象形。玉钺与石斧相近,是一种礼器。中国古代重祭祖,也即祭种,祭“且”。“且”为祖之字根。循着廖平原先生的观点,我们对屈家岭遗址这一中心聚落的社会结构和祭祀情况可作一些探讨性分析。屈家岭遗址成熟的稻作农业已经显示其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遗址上先民们有了财富积累并已初步集中,社会结构已经出现分化。作为文明形成的特征之一,祭祀活动必然会盛行,并受到崇尚。这件“玉钺”,顾名思义,是以极其稀有的玉来制作出的一件“钺”,非一般工匠、非一般技术能够加工出来,很难想象史前三苗先民们会拿它来作一般砍伐工具。因它已是权力的代名词,所以,一个部落特别是像屈家岭遗址这样的史前大型中心性聚落,其首领能够拥有这样一件“玉钺”,无疑是军事指挥权、政治、经济活动统领权的象征。人们祭拜祖先和神明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礼品。当钺成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用于统领指挥和祭祀礼仪之后,无比稀罕和珍贵的玉钺当然成为一种政治的、精神的信仰之物,更是让人有所寄托和崇拜的神明之物。
屈家岭遗址自1954年冬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时被发现以来,前三次发掘均为时间较短的断续发掘,只有2015年开始的第四次发掘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总计发掘面积也极其有限,因而这件稀罕的“玉钺”暂时制约了我们的想象。相信随着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件玉钺迟早会说出让世人更加明白的史诗性“话语”。正所谓:青玉袅袅烟似起,灵钺祭礼通天意。
玉钺何来?

遗址公园内青木垱河一景
众所周知,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梯状分布。屈家岭遗址地处大洪山南麓,地理坐标30°50′13〃N,112°54′14〃E,其北面是太子山主峰上的白龙观。目前已探明的十二处遗址以环壕内核心遗址为中心分布于周围丘陵岗地,东南部是典型的山前平原,为江汉平原与西北连绵起伏的群山接壤处。这里三面环山,自古以来青木河和青木垱河分别自北面的不同方向两次交汇而过,周边沟渠纵横,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较多,是一处桃花源似的鱼米之乡、生态宜居之处。一般而言,这里并非产玉之地,安居于此的三苗先民们稻粟兼种,制陶信陶,同时也信奉玉质器物。那么,这件制作规整、光滑细腻、一面有明显沁石的史前玉钺到底从何而来?因为大荆楚物产丰饶,系本地产出?因为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传播,自北面而来?因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交流活动,自东面而来?略知屈家岭遗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人,不能不引起无限的遐想,所以有必要对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和周边出土的史前玉石钺加以梳理,以“追查”屈家岭遗址出土的这件玉钺来自何方。
本土之钺?我国古玉研究权威专家杨伯达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玉器全集》一书的概述中说,我国“长达六十万年的南北广大地区出土的玉器之原材,除了个别的之外,均取之距其住地不远的地点,也就是‘就地取材’之美石,不是角闪石玉。”和田角闪石玉是我国众多玉材品种中十分珍贵的一种。古书有“荆山之玉”一说,意思是湖北南障一带出产宝玉。相传和氏璧就出自于此。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的玉石资源至今已发现松绿石等十余种。屈家岭遗址发现的这件玉钺看上去是由一种青玉精心加工磨制而成。长江上中游少量出产这种颜色偏向深绿、通透性一般的青玉也未为可知。大量考古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史前玉钺普遍分布于中原、北方、华南、长江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1月发表的《长江中游史前玉器的起源与初步发展》(田广林,蔡憬萱,第37席卷第1期)一文中说,“其实早在距今约8000年前,长江中上游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玉器……丰富的玉器考古材料表明,长江中上游一带也是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该文最后综合分析说,“根据重庆大溪遗址发现玦类玉器加工过程所剩余的玉芯、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曾发现疑似玉器加工作坊的灰坑迹象,可知本地区早期玉器均出于本地制造。”“到了大溪文化时期,绿松石质地玉饰与透闪石等其它质地玉器交相辉映,并为本期玉器最常见的玉材。”“早在本地区玉器起源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穿孔、打磨、切割、抛光、乃至雕刻等工艺技术,都已普遍用于玉器的制作加工。”从该文所持的观点——长江中上游地区也是中国玉器的起源区域之一,由此推断,屈家岭遗址发现的玉钺,有可能出产自本文化区域,非其它文化区域传来。辛丑年五月,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在屈家岭举办了纪念湖北考古奠基者张云鹏与王劲先生的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朱乃诚先生在纪念活动座谈会上说,江汉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成为中国玉器制作和玉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上千年的历史积淀。这是屈家岭文化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贡献。朱乃诚先生重申的这一观点,无论是在2014年纪念屈家岭文化发现60周年座谈会上,还是发表在2014年第3期《南方文物》期刊上,都得到了业界和社会的认同。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为兴盛和强势的一种文化,其先民们既然能够制造出用于生产或者礼仪之用的石钺,也就有可能自己加工制造出更加高级的玉钺。江汉地区玉文化发展至最高水平的代表,一定有一个早于4000年前后、长期的、渐渐的过程,屈家岭遗址也应该是对应时期的玉文化发展主体。
北方之钺?黄河流域与屈家岭文化同时或略早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都发现过精美的玉钺,而且年代稍晚的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游石峁文化、下游的龙山文化出土的玉钺遗存中,都有青玉的身影,且其形制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差异性。我们知道,青玉为五大软玉(白玉、黄玉、青玉、墨玉、碧玉)之一,并且,青玉作为软玉主要出产自新疆和田,还有若羌、青海等地。屈家岭遗址的这件青玉钺是否来自北方或受北方影响呢?如果此说成立,则有两种可能存在的方式:
其一,直接从北方其它文化圈传来。距今5000年前,中华大地除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强盛文化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也是一种文明起源性的强势文化。此时屈家岭文化因素发生强劲的扩张,屈家岭文化在与北方大的文化碰撞中,处于强势北上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北方的华夏集团和三苗集团在不断碰撞的形势下,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也在加快进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说过,“各个区域的文明彼此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流,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后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以玉为贵的观点、龙的信仰、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礼仪制度、和合思想等。”这都是玉钺有可能直接从北方其它文化圈传来的背景和条件。2020年12月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家岭遗址联合考古队先后通过《湖北日报》、人民网、新华社、学习强国等媒体或平台,正式披露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发现目前长江中游最早的粟遗存时说,这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这里的最早证据。那么,屈家岭遗址发现的这件玉钺,是否也是从北方传来的呢?进一步讲,它又是因为什么、如何从中原文明之地传到长江中游这片史前文明之地的呢?在上述相关报道中,我国著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认为,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炭化粟粒,可能是因江汉平原通过汉水中游地区特别是随枣走廊与南阳盆地相连,而南阳盆地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和碰撞的枢纽地带。由此,这件尊贵而稀罕的玉钺随之而来,自然而然传到屈家岭遗址,便是大概率的事了。英雄会盟?俯首称臣?物物交换?种种猜想,出自屈家岭遗址的这件稀罕宝物都是长江中游一段文明史的见证。
其二,从扩张至北方的屈家岭文化圈传来。近年,我国史前考古不断取得令人兴奋的重大发现。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的黄山遗址发现了10座距今5000多年的玉石器生产作坊,其中屈家岭文化时期玉石器生产作坊址有7座,还清理出屈家岭文化以随葬大量猪下颌骨为特色的玉工族群墓葬90多座。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大型玉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大遗址。“此次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地区、距今5000多年的关键时间为研究中华文明形成提供了关键材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黄山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马俊才说。在湖北襄阳市保康县穆林头遗址,考古队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于整个发掘区,遗址墓葬分布密集,随葬品数量丰富、器物精美。其中一处较高级别氏族墓地,从随葬玉钺、玉璇玑等权力象征物看,墓主应为一酋长级别的首领。这是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考古的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屈家岭文化有重要价值。这两处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说明屈家岭文化在向北扩张之后,先民们在一些控制地带已经形成了生产、生活较为稳定的社会,同时又与长江中游、汉水之东的屈家岭文化核心区域保持着相应的联系。那么,在本文化圈势力范围内的北方就地取材、就近加工玉钺等玉类器物之后,这件玉钺传回屈家岭遗址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东方之钺?居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与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一衣带水,而且屈家岭文化所处时期与良渚文化有所重叠。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相互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能呢?
《中国古代礼器——玉钺的前世今生》 一文还说,鼎盛时期的玉钺,形式规整、图文精美,目前则多集中发现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晚期墓葬中。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在近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良渚玉器》一书序言中说,“中国史前玉器以良渚文化最为发达”,“良渚遗址是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巨大群落。古城中心有莫角山等类似宫城的高等级建筑和钟家港的玉器等手工业作坊……”众所周知,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主流学术界广泛认可,其数以千计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文明古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世界。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圣地的实证,向我们展示出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就是这一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
在世界文明的起源、交流和发展过程中,尽管古人类氏族或者部落之间的来往因为山高林密、江河湖海造成地域阻隔,相对封闭,但一个地方的先进文化和文明之物还是会像风一样传播开来。南稻北上,北玉南下,通过考古发掘研究均有不争的实证。良渚既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的玉器王国,其举世瞩目的先进玉文化就有可能溯江而上或者通过同为第三级地势的坦途,影响到屈家岭。

屈家岭遗址博物馆
总之, 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为屈家岭文化的命名之地,这件魂系汉水之东史前农业文明的“玉钺”,曾经演绎过怎样的历史兴盛故事,还需要当地考古及各类古文化研究专家以这种极其重要的礼器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更进一步揭开其神秘的历史面纱。(文章来源: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作者:周丽 陈志华 李珊珊)